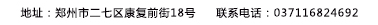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小羊,脸叔的小助手。提起全职妈妈,我们会想起《三十而已》里的顾佳,《82年出生的金智英》的金智英,想起北京的“顺义妈妈”和“海淀妈妈”。我们讨论的是划分到私人领域不被支付的劳动——家务,讨论不被看到的女性和她们的需求——女性被期待让家成为让每一个人安宁和休息的避难所,除了她们自己。但当我们把目光看向都市边缘、乡镇地区,看向更远的四川大山和沿海稻田的更深处。处在农村地区的全职妈妈,在资源更为贫乏的条件下,她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她们人生受到的限制更多。在女性意识蓬勃的今天,我们需要清晰地看到:在农村做一名“全职妈妈”,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农村全职妈妈的日与夜 9月,圣女果秋播前需要整地,天微微亮时,阿云和丈夫已经把装满一车有机肥的“四不像”(四轮拖拉机)开进田里。阿云穿着做饭带的粉色围裙,戴着同样老旧的粉色袖套、手套,脚底踩着一双黑色水田靴,头上歪歪斜斜戴顶草帽,一铁锹一铁锹地把车里倒出的有机肥洒向田里。 等到天光大亮,阿云草帽下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打湿,一缕缕贴在脸颊上。干农活时最不需芥蒂的就是晒和脏,她脱掉围裙和草帽,只穿一件黑色的短袖,手里的工具从铁锹换成了铁锄。日头猛烈,光线把脚下的四亩地切割成阴凉和暴晒两部分。阿云的孩子们已经醒来,跑到地里玩耍,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拿着小铁铲在阴凉处蹦蹦跳跳地铲地玩。阿云站在光亮处,胸前是交叉的背带,她微微佝偻,重复着锄地的动作,背上背着只有5个月大的,她最小的女儿。 耕好播种的床土后,太阳开始西斜,晴天的下午是起垄定植的好时候,拉滴管,敷膜,要时刻留意着两个玩耍的孩子,也要哄着怀里哭闹的孩子。阿云一刻也没有闲下。全部的地膜铺好了,忽明忽暗的云终于带来一阵风,一整天未歇的汗已经放凉,阿云擦干净脸换了一件粉色的短袖,在夕阳下长长舒了口气。 图 施肥、整地、铺膜后的圣女果果园 阿云生活在广东西南部的湛江遂溪县,这里雨量充足,终年润湿,是“湛江市区后花园”。在遂溪岭北镇上,不同水果的生长轨迹划分了阿云的日历,9月圣女果整地种植,10月火龙果筛花和采摘,11月给草莓摘叶拔草,果实甜蜜,背后却是阿云日复一日的劳作。 遂溪多雨,雨后泥巴厚重地粘成块,不能用机器,只能人工起垄,一天下来,即使带着手套,阿云的手掌还是被磨出4个水泡。草莓种好后需要下干肥,阿云一手拎着小桶,另一只手从桶里拿出一小撮干肥均匀地放在每颗草莓上。顺着田垄从田地这头走到那头,一直弯着的腰早已酸痛不堪,站直时膝盖直打颤。拔草时总要蹲着,阿云把背后的孩子转到胸前抱着,放在大腿上,一边拔草一边抖腿,断断续续哼唱着哄孩子睡觉。 干农活是很累,可阿云说不上做农活和做家务,哪个更累。一年中,阿云的12个月被水果种植和采摘的农时峻烈穿过。落地到寻常的每一天,无尽头的家务劳动则贯穿了阿云的日与夜。 图 阿云背着孩子搭晾衣服 在广东省,像阿云这样的农村全职妈妈超过万,放眼到全国,这个数字可能会超过一亿。在农村的全职妈妈,不仅要肩负家庭中的生产劳动,在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中耗尽芳华,同时,她们还要承担城市全职妈妈的职责:孩子教育、老人照料的妻职和母职。双重的重压之下,她们的生活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 每天6点半,阿云起床,先送8岁的大女儿去镇上的学校,回来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洗衣服,晒衣服,晒完衣服去田里干活,回来给一家人做午饭。有时候手头的饭没做完,就要接孩子放学回来。等饭端上桌,喂更小的孩子吃完饭,阿云顾不得自己吃口,便又要哄小孩们午睡。然后是洗碗,喂狗、喂鸡,下午两点钟送大女儿上学,回来后去田里给圣女果绑枝。等光线在叶间消逝,阿云知道,该回家做晚饭了。 无论做什么,施肥或者晾衣,无论在哪里,逼仄昏黄的厨房或是宽阔明亮的果园,阿云的脚边绕着寸步不离的两岁宝宝,她的胸前总缠绕着背带,背带里是只知摇摆和啼哭的婴儿。 打工、返乡嫁人,农村全职妈妈的人生轨迹阿云是遂溪岭北镇本地人。家里6个孩子,阿云最小,往上是5个姐姐和1个哥哥。年纪最大的长姐与阿云相差12岁,阿云从小被长姐带大。这是个一心想多要几个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姐姐们和阿云的性别感到遗憾,既无心,也无力在女儿们身上付出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