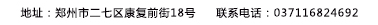|
后记意大利作家、寓言家和童话采集者伊塔洛?卡尔维诺坚信幻想和现实间的联系:“我习惯将文学视为知识的探求,”他写道,“巫师在面对部落生活中的危殆处境时,其对应之道是抛去他的肉体重量,飞向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感受层面,去寻找力量改变现实的面貌。”安吉拉?卡特不会这么板着脸许下相同的愿望,但是她将幻想和独出心裁的渴望结合起来,这与卡尔维诺写的巫师飞行很相像。卡特具有巫师轻盈的智慧与才思——有趣的是,她也恰好在最后两部小说中探索了有翅膀的女人的形象。《马戏团之夜》中的空中飞人女主人公飞飞可能是像鸟一样被孵出来的,而在《明智的孩子》中,双胞胎欠思姐妹扮演了各种仙子和长羽的角色——从以童星身份首次登台亮相,到后来游戏好莱坞,出演壮观奢华的《仲夏夜之梦》。精怪故事也为卡特提供了飞行的途径,即寻找、叙述另一个故事的途径,和在头脑中改变事物的途径,正像许多精怪故事中的角色会改变形体一样。她创作自己的故事,将贝洛的《鹅妈妈的故事》以及其它家喻户晓的故事改写成炫目、情色的版本。在《血窟》中,她将美女、小红帽和蓝胡子的最后一个妻子从色彩柔和的育儿室中抽离,投入女性欲望的迷宫。卡特一直广泛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从西伯利亚到苏里南,她从丰富的资源中找到了这里收集的故事。其中仙子、精灵意义上的精怪并不多见,但是故事发生在仙境中——不是被粉饰和庸俗化了的维多利亚式精灵王国,而是更加黑暗的梦幻疆土,里面充满鬼魂与诡计,懂魔法会说话的动物,还有各种谜语和诅咒。《十二只野鸭》中,女主人公发誓既不说话,也不哭笑,直到把中了魔法、变成动物的哥哥们拯救出来。女性的话语和声响,她们/我们的喧嚷、欢笑和哭泣——这类主题贯穿安吉拉?卡特的作品,影响着她对民间故事的热爱。《魔幻玩具铺》中美丽的玛格丽特舅母被银项圈卡住不能说话,而这个项圈是邪恶的木偶大师,也就是她的丈夫,做给她的结婚礼物。与之形成对比,民间故事不仅在诉说,而且在充分诉说女性的经验;女性常常是故事的讲述者,比如合集中的一则富有活力、引人发笑、极具卡特风格的故事(《打老婆的理由》)。安吉拉?卡特对女性的偏护之情在她所有的作品中燃烧,却从来没有将她引向任何传统形式的女权主义,不过在这里,她沿用了一项原创而有效的计策,从“厌恶女性”的虎口夺下了对女性“有用的故事”。她年的论文《萨德的女性》从萨德身上挖掘出一个令人眼界大开的导师,他讲授男性和女性的现状,并照亮了女性多态欲望的边缘地带。在这本书里,卡特颠倒了一些劝诫性质的民间故事,摇出它们曾经表达的对女性的恐惧和厌恶,从中创造出一套新的价值,颂扬坚强、坦率、热情、性别特征显著、永远都不屈服的女性(参见《逆流而上的老太婆》和《信的花招》)。在《明智的孩子》中,她创造了多拉?欠思这个女主人公,她是歌舞女郎、扮演轻佻女仆的演员、杂耍剧院的舞者,是低下、遭人鄙夷的茫茫贫苦大众中的一员,也是一个私生女和从未结婚的老太婆(投错了胎,错生在贫民区里),但是所有这些耻辱都被兴高采烈、津津有味地拾起,而后抛撒向空中,好像婚礼上数不清的五彩纸屑。书中压轴的《伸开手指》是来自苏里南的一则严厉的道德故事,讲的是要与他人分享自己获得的赠与,这则故事也显示了安吉拉?卡特对慷慨的重视。她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想法、才思、犀利不含糊的头脑——心意坦诚却从不多愁善感。这里她极为喜爱的一篇是俄罗斯的谜语故事《明智的小女孩》,其中沙皇向她的女主人公提出了不可能的要求,可她眼都不眨一下就办到了。安吉拉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令人满意,但是“没有人受到羞辱,人人都得到了奖赏”。该篇收录在“聪明的妇人、足智多谋的姑娘和不惜一切的计谋”这一章中,里面的主人公本质上是个卡特式的人物——从不羞愧,毫不畏惧,像雌狐一样听觉敏锐,同时又具有不露声色的清醒判断。她以沙皇的困惑为乐,却不想让他受到羞辱,这是极其典型的安吉拉的性格。临终前,安吉拉没有力量按照原定计划为组成本书后半部分的《悍妇精怪故事集第二卷》作序,但是她在手稿中留下了四条令人费解的笔记:瓦尔特?本雅明说:“每个真实的故事都包含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故事的非迷惑性帕斯卡说:“再贫穷的人死时也会留下些什么。”精怪故事——狡黠与兴高采烈这些词句尽管支离破碎,却传达了她的哲学。她尖锐的批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表现出的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忽略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文学——也许更多——都是由不识字的人创作的。她喜欢民间故事中可靠的常识,主人公直截了当的目标,简单的道德区分,还有它们所提出的狡猾计谋。它们是弱者的故事,讲的是狡黠和兴高采烈最终获得成功;它们是实际而不浮夸的。作为一个长着翅膀的幻想作家,安吉拉始终将目光投向地面,坚定地注视着现实。她曾经说过:“精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去向另一个国王借一杯糖。”此类别的女权主义评论家——尤其是在年代——不肯接受诸多故事因循社会习俗的“大团圆结局”(比如“她长大以后,他同她结了婚,于是她当上了皇后”)。但是安吉拉懂得满足与欢乐,同时又相信精怪故事的目的不是“保守的,而是乌托邦式的,事实上也就是某种形式的英雄乐观主义——就好像在说,有一天我们会获得幸福,哪怕它不能持久。”她自己的英雄乐观主义从未弃她而去——就像她故事中精神饱满的女主人公,她在患病直至离世的那段时间里表现得机敏、勇敢甚至幽默。鲜有作家拥有其作品的优秀品质,她却人如其文。她的想象力耀眼迷人,通过大胆而令人眩晕的情节、准确而狂野的意象,通过那一系列精彩的“亦好亦坏”的姑娘、野兽、无赖还有其他角色,她使读者屏住呼吸,直看着英雄乐观主义的氛围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聚拢过来。她拥有一个真正作家为读者重新创造世界的天赋。她自己就是个明智的孩子,她有一张表情丰富的脸,有时会反讽地撅起嘴巴,眼镜后面带着揶揄,时而闪闪发光,时而流露出梦幻的神情。她长长的银发和幽雅的谈吐给人“仙后”的印象,只是她从来都不显得飘渺、脆弱。尽管青春的自恋是她早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她自己却是个特别不自恋的人。她声音柔和,带着讲故事的人推心置腹的语气,充满了生动的幽默。她说话时似有某种切分的节奏,因为要时不时地停下来思索——她的思想使她成为最令人愉快的同伴。她很健谈,学识渊博却不炫耀,能够手术刀般精准的表达某种顽皮的领悟或是艰难的判断,亦能够轻而易举地道出许多新想法,将典故、引语、滑稽模仿和原创发明编织在一起,一如她的散文风格。“我有个推测……”她总是这样自谦道,然后会说出某个别人未曾想过的见解,某个或俏皮或意味深长的悖论,概括起一个趋势、一个瞬间。她可以像王尔德一样机敏,闪着旁敲侧击的古怪幽默,然后她会继续下去,时而惊得听众目瞪口呆。安吉拉?卡特出生于年5月,父亲休?斯托克是报业协会的一名记者,出生在苏格兰高地,整个一战期间都在服兵役,然后来到南方的巴勒姆工作。他常带女儿去杜丁的格林纳达电影院看电影,在那里,建筑(阿尔罕布拉风格)和电影明星(《南海天堂》里的珍?西蒙丝)的魅力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关于诱惑和女性之美,安吉拉写下了某些史上最为浮华、时尚和性感的篇章,在她的语汇中,“漂亮时髦”和“魅力无穷”是欢乐与赞美的关键词。她母亲的母亲来自南约克郡,这位外祖母对安吉拉来说十分重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某种自然的权威和与生俱来的野性,如今我对那一切心怀感激,但是当我在南方找男朋友的时候,那种钢铁般的性格可不太好对付。”安吉拉的母亲是个通过了高中学术级考试的姑娘,“喜欢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年代,她在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当收银员,并且通过了相关考核,她希望女儿也能一样。安吉拉进了斯缀特姆文法学校,一度幻想成为埃及古物学者,但是毕业以后,她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克罗伊登广告报》当学徒。作为新闻记者,安吉拉被想象所困(她喜欢俄罗斯故事讲述者的套路:“故事讲完了,我不能再瞎编了”),于是转写唱片专栏和专题文章。她二十一岁时首次结婚,丈夫是布里斯托技术学院的化学老师,同年,她开始在布里斯托大学修习英文,选择专攻中世纪文学,这在当时绝对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中世纪文学的形式——从寓言到故事——以及笔调的多元性——从粗俗到浪漫——在她自己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乔叟和薄伽丘一直都是她特别喜爱的作家。最近她也在接受好友苏珊娜?克莱普的采访时回忆起当时在咖啡馆里同“情境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交谈的情形:“那是六十年代……我非常非常不快乐,但同时又是完全快乐的。”这一时期,她首次开始培养对民俗学的兴趣,并同丈夫一起发现了年代的民谣与爵士音乐圈。(在较近的一次民俗学会的沉静集会上,她深情地回忆起反传统文化盛行的日子——那时候会有成员带着肩上的宠物渡鸦一起出席。)她开始创作小说,并在二十几岁时发表了四部作品(《影舞》,;《魔幻玩具铺》,;《数种知觉》,;《英雄与恶徒》,;此外还有一个写给孩子们的故事:《黑姑娘Z小姐》,)。她获得了大量赞誉和奖励,其中包括萨默赛特?毛姆奖所规定的旅行,她遵守了要求,用这笔钱逃离了丈夫(“我想毛姆是会赞同的”)。她选择了日本,因为她很推崇黑泽明的电影。日本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年起,她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她之前的小说——包括残忍、紧凑的挽诗《爱》(年创作,年改写)——显示了她巴洛克式的创造力,以及对色情暴力的直面,这种暴力不但出自男性,而且也出自女性:她早早地划好领地,男人和女人在上面厮杀,常斗得鲜血淋漓,而里面也多是面临大难时的幽默。从一开始她的文笔就是华丽丰富、陶醉于辞藻的——她的语汇生动而感性,描写的是各种身体特征、矿物、花卉和动物——同时她也涉及了陌生感的主题。然而日本给了她一种看待自身文化的方式,加强了她从熟悉事物中创造陌生的能力。这段时间她也接触了因为“五月风暴”而落脚日本的法国流亡者,由此加深了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联系。在日期间,安吉拉写了两部小说,尽管它们并不直接与日本相关:《霍夫曼博士的地狱欲望机器》()和《新夏娃的激情》(),里面当代的冲突变成了怪诞、多样的流浪汉寓言。她并没有像同时代的某些作家那样赢得畅销书的大笔收入(她常沮丧地表示外面仍旧是个男子俱乐部,但却不是真的耿耿于怀),也不曾入选主要奖项,然而她享有更多国际上的好评:她的名字从丹麦一直传到澳大利亚,她也反复收到教学邀请,并就任于设菲尔德大学(-8)、普维敦斯的布朗大学(-1)、阿德雷德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7)。她协助改变了战后英文写作的发展方向——从萨尔曼?鲁西迪到珍妮特?温特森再到美国寓言家罗伯特?库弗,许多作家都受到了她的影响。远离英格兰帮助她揭示了女性与其被征服之间的密谋。她在批评文集《被删除的秽语》中回忆道:“好多年里,我都被告知应该想什么、怎么做……因为我是个女人……但是后来我不再听他们的了……我开始还嘴。”从日本回来以后,她在一组极其犀利的文章(年集成《没有什么神圣的》)中探讨了各种不容置疑的习俗和当时的时尚(从鲜红唇膏到D?H?劳伦斯笔下的长筒袜)。安吉拉从来都不是个提供简易回答的人,她以坦率的态度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谈及面对残酷现实时,她喜欢半反讽地说:“苦活儿——但总得有人去做”,她也常常赞许地说某人“并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弱者”。她的出版商兼朋友卡门?卡莉尔以悍妇社的名义出版了她的作品,她从该社成立起就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帮助将文学中的女性声音确立为独特和先入的,使之成为在后帝国时代虚伪、僵化的英国打造新身份的一种重要工具。因为尽管对现实有着敏锐甚至悲观的把握,安吉拉?卡特始终相信变化:她会谈及自己“幼稚的左倾主义”,但是她从来不曾放弃。美国评论家苏珊?苏雷曼称赞说安吉拉?卡特的小说真正为女性开拓了新领地:她使用具有叙述权威的男性声音,并把它模仿到了讽刺的程度,使得规则发生改变,梦想变得难以驾驭、焕然一新、易于接受“叙述可能性的增加”,这些梦想本身就预示着一个或许不一样的将来;这些小说也“拓宽了我们的思路,让我们认识到在性的领域什么是可以梦想的,由此批判了所有过于狭窄的梦想”。安吉拉最喜欢的女性象征是魏德金戏剧中的露露,而她最喜欢的明星是在《潘多拉之盒》中扮演露露的露易丝?布鲁克斯。露易丝/露露很难算得上是拒绝传统女性特征的人物,相反,她们将女性特征发挥到极致,使其性质发生了变化。“露露的性格非常吸引我,”她会这样不动声色地说;她借鉴了这个角色的特点,创造了《明智的孩子》里浪荡、喧闹、精力充沛的舞台女主角。露露从不巴结逢迎、追名逐利,也没有内疚和悔恨。照安吉拉的说法,“她的特点就是,她使得多态的任性变得好像唯一的存在方式”。她曾说过,如果有个女儿,她会叫她露露。她喜欢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是“经典大伦敦议会”式的,但是撇开这些顾忌不谈,她也是个见解独到、尽心尽力的政治思想家。她怀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将“低俗”文化以及大众语言、幽默的粗俗活力肯定为持久、有效的生存手段,《明智的孩子》()正是源于这样的思想:她的莎士比亚(小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包含了他的绝大部分人物和剧情)不为精英阶层创作,而是将想象力扎根于民间,从中汲取能量和经验。安吉拉与马克?皮尔斯找到了幸福,她患病的时候,马克正在接受小学老师资格培训。安吉拉时常说起孩子们容光焕发的样子,说起他们无法形容的美丽和他们的爱;她与马克的儿子亚历山大出生于年。有时候,面对一个伟大的作家,人们容易忽略他们所带来的欢乐,正如评论家们寻找的是意义与价值、影响与重要性。安吉拉?卡特热爱电影、杂耍、歌曲和马戏,她自己也深谙娱乐之道,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她在这个集子里收录了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故事,讲一个苏丹的妻子日益枯瘦,而一个穷人的妻子却过得快快乐乐,因为她的丈夫喂她“舌头肉”,也就是故事、笑话和歌谣。这些就是使女人欣欣向荣的东西,故事这样写道;它们也是安吉拉?卡特为了使他人活得欣欣向荣而如此慷慨赠与的东西。《明智的孩子》最后写道:“唱歌跳舞是多开心的事!”她自己没能欣欣向荣地活下去实在是让人难过到无以言表。她去世之后,报纸上、广播里都充满了对她的哀悼。如果她还在世,会惊讶于人们的哈尔滨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专科医院宁夏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哪家好
|